「译」乾隆第一套功臣像的八个例子(二)
上文书说到,准噶尔战争之后乾隆接连进行庆功仪式,另一方面,大量战争及其相关的图像开始投入制作,本文简单介绍其制作思路以及傅恒画像的一些特点。
译自 Tabo Tsang
Portraits of Meritorious Officials:
Eight Examples from the First Set Commissioned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除了这些浮夸的庆祝仪式以外,关于战争的细节也被仔细地收集,因此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战争以各种各样的媒介形式记录下来。乾隆在战争期间创作的两百多件甚至更多的战争诗歌都被整理收集起来,然后被雕刻在石头上,放置在坐落在紫光阁后,用来展览战利品和其他战争纪念品的武成殿里。一份关于战争的完整的记录被写下来,刻在石头上,放置在国子监里。主要的战争中个人的功勋也被雕刻在石头上,放置在东突厥斯坦的战略要塞,用作对殖民地可能的反抗进行的视觉威慑。

平定准噶尔勒铭碑拓本。
在图像制作的方面,作为一个充满激情的艺术赞助人,乾隆要求他的宫廷画师们快马加鞭,抓住这一黄金机会将他晚年称为「十全武功」的功勋中的前六项永久地纪录下来,流传于后世。在这些大型的图像中,是战争中打斗场面的纪实,各种胜利后的庆功宴,以及单个的功臣的画像,比如阿玉锡或者玛瑺,正在重现他们的英勇的瞬间。但是我们将注意力聚焦在一套一百幅功臣画像中的三个版本上。
武成殿。
1759年,战争胜利结束后,乾隆就有了奖励这些有功之臣的想法。一百个功臣被谨慎地挑选出来,既有武将,也有文臣。随后这一百位功臣被分进了两个组。第一组被视作一等功臣,而第二组稍逊色。据此,每一个功臣都收获了相应的报酬。除此之外,他们也将被画像铭记。第一组的成员被乾隆亲自题写的称颂所给予荣耀。而他们在第二组的同仁们,则无法得此殊荣,只能得到由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等乾隆的文艺顾问们共同题写的诗句。
基于现有的例子和一些文字的资料,这一系列的画像至少制作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为绸缎笔墨绘制,展示在紫光阁。至今(译者注:1992年),这个版本有七幅作品已经公之于众。这些挂轴通过不同的姿势来展现个体的性格。在每一幅画像上是用满语和楷书汉语书写的题词。题词包括了官员的名字,他的功勋的级别,一份称颂,以及创作者的名字,和时间「乾隆朝庚辰年春(译者注:1760年)」,一枚钤印「乾隆御览之宝」,印在两种语言的文本之间。
第二个版本是为了皇帝自己的意趣而制作的。形制也从大规模的挂轴变成了更加暧昧,更好阅览的手卷。这个版本被分入两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包括一个展示了五十位功臣形象的卷轴,笔墨绘制在纸上。只有第一个呈现了有卓越功勋的功臣的卷轴,被记录在了皇家艺术目录《石渠宝籍续编》中,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它由金廷标完成,完成时间是上文所说的大挂轴的版本完成的同年六月。这个手卷立即吸引了乾隆的注意力,他亲自把那些更加重要的功臣像的赞颂誊抄到了手卷上。除此之外,他还在手卷的各个部分盖了不少于六十二个印章。目前第一个手卷只有一个分段已知存世。造办处的档案告诉我们,一年后同一位画家接到了制作第二个卷轴的命令。然而,由于资料的缺少,它的完成日期我们尚不清楚。
根据造办处的档案,第三个版本也被我们找到。证明其被创作的条目被记录在乾隆二十八年十月的十四日(1763)和次年五月的十九日。前一条记录了两天前的命令,要求前五十位功臣的图像将由水墨和色彩在丝绸上呈现出来,并且由金廷标、艾启蒙和珐琅彩部门的工匠们一起完成。金廷标负责将第二个系列中的图像形象放大到挂轴的大小,艾启蒙则负责深入脸部,珐琅彩工匠们负责衣物和武器的绘制以及色彩。第二条档案简单记录了后五十名功臣的制作前的要求-衣服的褶皱需要由画院的画家完成。这样的人事安排的变化也许表现了乾隆对于造办处珐琅画匠们在第一个系列的表现的不满意。至今我们尚没有发现任何第三个版本的遗存。然而,这一系列和第二系列都是在金廷标的领导下完成的,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一版本绘画风格与第二版本类似,但被放大到了第一版本的规格。
威廉希尔体育在线平台傅恒像。
目前存世的第一版本中的七幅挂轴大画中,有三幅都是第一序列的功臣(前五十名)。分别是傅恒,纳木扎尔和阿玉锡,其他四幅则来自于后五十位功臣,分别是占音保、严相师、巴岱、那木查尔。傅恒的画像上的赞颂是:
“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世胄元臣与国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绩/定策西师惟汝予同/鄼侯不战/宜居首功/乾隆庚辰春御题”
傅恒来自于富察家族,是满族镶黄旗成员。他的姐姐是乾隆的第一任皇后。作为皇帝的小舅子,他的仕途非常顺畅。年幼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御前侍卫,经历许多次升职后,终于在1748年成为了总侍卫。同年,负责平定四川西部金川区域的两名将军因为无能而被斩首。傅恒取代他们,被全权委任处理那些意识到长久抵抗无用而投降换取和平的反贼们。尽管从未亲身参与过任何实际的战斗,傅恒仍被认为具有主要的贡献。
1754年,当乾隆想要利用准噶尔混乱的局势来驱逐野蛮的蒙古人时,他向自己的高级官员们寻求建议。所有的官员都表示了对于这场注定代价巨大又危险重重的战争的不赞同,并且援引雍正八年在和卜多和巴里坤的失败为先例。傅恒却是唯一一个支持皇帝的提议的人。对于他及时的支持,乾隆充满了感激,甚至于在1755年概括第一场对于准噶尔的征服的胜利时,乾隆公开承认了他的信臣-傅恒的重要作用。尽管傅恒又一次没有亲自上阵,他仍然被认为,就像萧何对刘邦创建汉朝一样,对于清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进而被封为“鄼臣”。据此,在一百位准噶尔战争功臣中,傅恒被认为“居首功”,排第一位。
在傅恒的画像中(宽:153厘米,高:95厘米),傅恒的姿势更是文臣而非武将。他身着盛装,值得注意的是盘龙纹的补服、冬帽上的红宝石尖顶和双眼孔雀羽毛都是他指挥金川战役时获得的赏赐。另外的凸显他高官身份的还有珊瑚项链,鼻烟壶,一个带着装饰的钱包和白色的飘带。所有的东西都被遮挡,只能看到部分。唯一彰显傅恒在军事上的功勋的是一把阔剑,也寄在腰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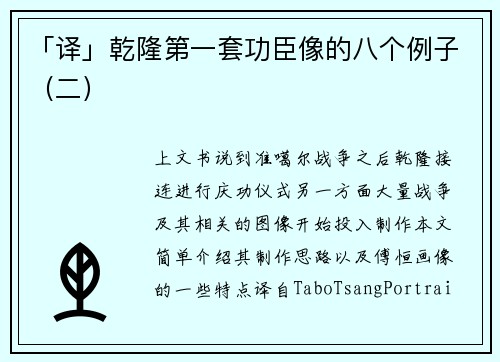
以一种并不舒适自然的姿势站着,傅恒双眼直盯观者。他的好肤色也表现了他富裕的生活。然而,像微皱的皮肤,眼角纹,双下巴这样的衰老的特征,也得到了表现。画作完成时,傅恒大概四十岁。这样真实而亲切的中年文官形象被使用色调渐变和高光来表现立体感的西方手法表现出来。相反,在人物的其他部分这样的立体感则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严格而拘谨的线条是典型的中国风格,是铁线描的样式。画家明显使用了分明的转角来作为个人的特色。因为整体而言色块是均匀分布的,因此各躯干间的主次关系不甚明朗。这种扁平感在与面部的栩栩如生进行对比时会显得更为强烈。另一个很少被讨论的不和谐之处体现在正面的脸部与倾斜的身体之间,后者的轴心、脚的转向都体现在这是一个向右倾的身体。
下期预告:继续翻译本文献的剩余部分,包括「阿玉锡画像轴」,「玛瑺斫阵图」的一些讨论,周更博主下线~